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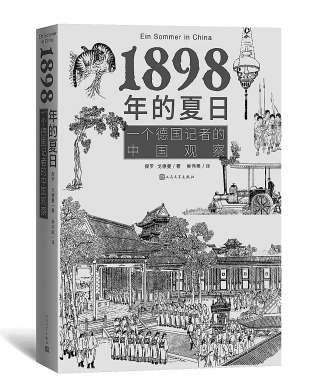
《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德]保罗·戈德曼 著 吴伟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一场戊戌变法震动全国,至今仍是史学热门话题。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4月10日,德国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法兰克福报》指派,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出发,前往中国进行采访。戈德曼乘坐的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出发后,穿越地中海,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亚丁湾,远航至欧洲式东方新城——新加坡。而后,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国腹地,进行详尽考察。途中,他先后采访了时任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长王存善、上海道台蔡钧。从上海又沿长江乘船而下,在镇江、汉口、武昌等地停留。
在汉口,戈德曼参观了欧洲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商业机构与修道院。在武昌,考察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聘德国教官主持训练的新式军队。在胶州湾的青岛、威海、芝罘(烟台)等地,深入探访了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地区。戈德曼此行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人物颇多。在烟台,他与原清政府驻欧洲外交官陈季同相遇。这是一位曾在欧洲大力推广中国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在天津,他采访了清政府陆军总领、直隶总督荣禄。在北京,他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这些在他回国后用德语写成了《一个夏天在中国》,在德国出版发行,但并未引起大众的关注。近日,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引进国内出版,更名为《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在书中,他也以记者的客观,披露了最初中国铁路规划过程中,欧洲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以及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相融相斥的情况和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通过与清政府不同级别官员的互动,他记录下清末官员对改革和与西方合作的不同主张以及民间对这种主张的不同反应。
武汉铁路逸闻
作为一名德国记者,戈德曼在这趟中国之行中,格外关注德国对中国的影响。他在书中讲到了现在的武汉作为中国铁路的全国中心,这一切的缘由与一个德国人有关。1891年设计过科隆火车站的德国建筑师锡乐巴,被委任替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做庭院设计。张之洞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员,在晚清的官场中独树一帜,他极力想凭借西方国家的协助,重新建设中国。当他第一次从锡乐巴的口中听到铁路时,他好奇地问“一条铁路?那是什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张之洞详细地听锡乐巴解释了铁路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想到,中国的发展需要铁路,当即就和锡乐巴商量先做一段小铁路试试效果,等了解更多后再想办法大量引进到中国来。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锡乐巴建了一条只有26公里的运矿铁路,张之洞看到真实的铁路后,非常满意,当时就想建造更多铁路,而且张之洞敏锐地看到了铁路在商业发展和军事上的大用途。于是他向朝廷打了报告,同时请锡乐巴作为设计师开始规划以汉口为核心的中国铁路网。锡乐巴设计了三条重要的路线,第一条是从汉口直到北京的北方线路,第二条是从汉口到广东的南方线路,第三条则是由汉口最大的贸易街往东经过南京到上海。张之洞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规划。锡乐巴通过实地考察在设计上解决了地形上的困难,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在最后一步上,却让德国人吃了瘪。
在戈德曼的眼中,这样一条铁路无疑会给德国的在华贸易带来大量好处,中国铁路的商业价值毋庸置疑,但当时的清政府无力拿出这么多资金来修筑铁路。在排除了自费、民间集资、政府修筑等各项筹款方式后,张之洞委托锡乐巴请德国政府帮中国建造这条铁路,毕竟开拓中国内地市场,在这么重要的路线上修筑铁路无论哪国都是求之不得的。但锡乐巴的申请却并非一帆风顺,通过媒体和议员的各方努力下,德国政府才终于答应帮中国修建这条铁路,并且派遣专业人员来中国测量建造,并与清政府共同筹措资金。
然而,列强并不允许当时的中国顺利修建这条重要的铁路,各国知道消息后纷纷走动关系向清政府施压。戈德曼以欧洲的国际关系给读者讲述了各国之间背后的利益链:比如汉口至北京的线路最后由法国和比利时人负责,看似是法国和比利时获益,实际上背后却是俄国人在攫取这段铁路的利益;再比如本来德国能够得到汉口至上海的东部线路,但是英国横插一杠子,整个德国国内为了修补和英国的关系而最终放弃这段铁路的修筑权。作者戈德曼详细解析了各国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为当初负责这个项目的德国工程师们感到悲愤,那些工程师到处受到排挤,而清政府只能用只给虚名不给实权的办法,弥补了德国人锡乐巴一个“中国铁路事务理事长”的虚职。戈德曼以德国的角度出发,他觉得如果德国政府再强硬些,不要惧怕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许德国的商贸能在中国有非常大的发展,而德国政府却一步步错失良机。
德国记者关于中国铁路的观察,让读者了解到清末那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传统的叙事中,中国作为被压迫者,习惯将西方列强看作是一个整体,但在德国记者的叙事中,我们看到德国竟然也成为了被瓜分的人,而清政府也在利用铁路建造权在西方列强之间搞平衡,也在“以夷制夷”。
拜访李鸿章
书中除了对中国事务的观察了解外,作为记者,戈德曼还采访了许多大人物,比如陈季同、荣禄和刚刚下野的李鸿章。李鸿章曾在1896年出访过欧美各国,这在当时引起轰动,因此作为外国记者可能最熟悉的中国官员非李鸿章莫属。西方世界认为李鸿章并不太像他们想象中的那种中国人,因此,戈德曼的中国之行,能够采访到李鸿章也算是圆满,可以从更高的层面上了解当时的中国。
在作者戈德曼提出对李鸿章的采访请求后,他有点惴惴不安,心中没底:“此时的中国官员都尽可能地回避与欧洲人士接触,如果在谁住处附近出现了一位欧洲记者,那他们很可能直接在大门外横摆上一根大木棍。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局面会如何演变,在这个节骨眼上,人心惶惶,所有人都避免进行任何会危及自身安全的访问。”但没想到李鸿章不太在意这些,他不但同意了采访请求,还决定第二天就对谈。这天正是欧洲军队进入北京的日子,作者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果然,在作者准备出门时,李鸿章派人送来一封信,“身体微恙”,取消见面。在保罗看来,这种态度是“典型的中国风格”——对德国记者的申请,答复是同意的,因为他不想直接反对而显得不礼貌,但同时他也力图避免这样的会面,因此在会谈举行的当日,他“生病”了!
几经波折后,作者终于见到了李鸿章,当时他并没有什么实际职务,但仍旧不甘心远离权力中心。从书中描述的两人对话看,李鸿章虽然没有直接发表对戊戌变法的看法,但也说得很明白了,他眼中“资深、有经验的官员,被不曾处理过国家事务的年轻一代排挤出去了。他们想从中获得利益,直到最终不能再走下去为止。经过这次危机,这些比较年轻的官员已经被铲除了。”发起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被他称为“不曾处理过国家事务的年轻一代”,而他无疑是“被排挤”的“资深、有经验的官员”代表。戈德曼继续问他:“那么您又为何失去了贵国皇帝对您的信任?”李鸿章回答道:“人们抨击我,认为我对外国人太过偏袒。他们称我是卖国贼。”作者紧接着写到,当李鸿章这么说时,脸部因怨恨而出现了一丝抖动。当他说到“卖国贼”这三个字时,爆出了一阵大笑。从这一篇的内容读者可以窥见,戈德曼的写作方式是相对中立的,他较善于观察,对事物不轻易下结论,虽然代表德国媒体,但仍旧是以专业记者的新闻笔法,记述多,评论少。他以一双西方的眼睛默默观察着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古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惊天巨变。
德国的“马可·波罗”
这本书被发掘出版其实也来自一个偶然。这本书的译者吴伟栗是旅居德国华侨。据吴伟栗说,他是在意大利的里亚斯特市的一家古董店偶然“淘”到这本书的:当他打算离开的时候,礼貌性地问了一下店老板:“您这里有来自亚洲的东西吗?”老板看了看他,想了一下,然后,用德语回答道:“我们店里有本一百多年前的书,里面写的是中国的故事,您有兴趣吗?”说着他从身后书架上找出两本书,小心翼翼地递给他。他看了一眼书的封皮:Ein Sommer in China,直译是:一个夏天在中国。这是一套上下两册的旧书,泛黄的封面与僵硬的纸张略有破损。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看,竟然全是古典字体的德文。他没有学过古典字体德文,一时间看起来有些吃力,也看不出什么门道和价值来,但他想,既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出版物,就当是古董买了也不错。
吴伟栗只用了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就买下了这本书,找到他懂古德语的朋友翻译。听着书中的内容,他不禁大吃一惊,感到这本书可能很重要——“外国人写中国的书有两本,一本是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一本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而这本《一个夏天在中国》时间正好介于这两本书之间。德国记者对1898年中国社会的描述,无论是什么样,应该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尤其是他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份,与清政府高级官员对话,一定能够为已有的历史叙述提供一些参照,说不定能提供我们更多关于戊戌变法,关于大清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我预感,这一定是一本记录中国历史的好书!”
保罗·戈德曼作为德国记者,对中国是持友好态度的,在反对纳粹等重大历史问题上,他的立场和气节也是令人赞赏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这本书中,他毕竟是站在德国的视角看中国的,有时候难免流露出一些俯视的观点,甚至偶尔会略有傲慢的口吻。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局限,也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我们在肯定这本书历史资料价值的同时,还需要对作者的表达保持独立的思考,理性地分辨相关内容。(作者 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