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王丽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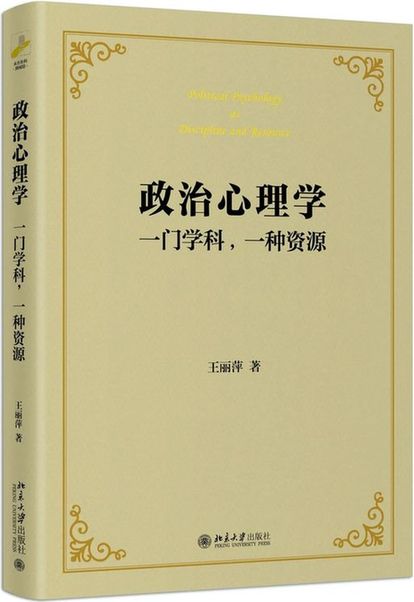
(本文为作者专著《政治心理学:一门学科,一种资源》序言。该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一
几年前,我作为燕京学者在哈佛大学访学,其间常去的燕京学社小楼一楼会议室有一副对联非常醒目:“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这是中国晚清官员陈宝琛在84岁时题赠燕京学社的。在燕京学社看到用汉字书写的对联本不应感到惊讶,与其内容类似的表达也很早就见于宋人陆九渊所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后由钱锺书先生概括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对联文字所传达的信息却使当时身处异乡的我在看到它的那一刻就深受触动。对联的后一句“心理东西本自同”所蕴含的东西方在人心道理方面存在共同点的令人感动的乐观信念,更是直接击中了我多年来的兴趣点。陈宝琛生活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中西交流日渐增多的特殊历史时期,又经历了中国从帝制向共和的重要转变。这副对联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经历的那个变动时代带给他的人生启示。
思考人心与人性是社会动荡时期人们尝试理解现实社会与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18世纪后期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欧洲社会处于政治动荡之中,思考群体问题常常被视为疗愈社会疾病的第一步。进入19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民主革命等多重变革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纽带和束缚,也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公民,可以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因此,理解和把握人的自然倾向并对其行为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就变得比从前更为必要了。
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所经历的剧烈而令人痛苦的社会动荡,使“群体”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群体心理开始得到研究,社会心理学也由此滥觞。政治心理学诸多领域的研究都起源于社会心理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心理学分享了共同的学科渊源,这也使政治心理学获得了对现实世界变化高度敏感的学科特性。
今天,人类社会正经历堪与19世纪相比甚至比19世纪更为剧烈和复杂的社会变革。如何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理解社会中人的行为倾向与选择,在人口流动增强、社会日益多元、参与扩大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变得愈发迫切和重要。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也成为政治心理学展示其应对现实社会问题重要潜力的契机。
二
二十多年前,凭着一股莫名的跨学科热情,我闯入了政治心理学的领地。这种跨学科热情与我1999年秋季学期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和研究的契机相结合,成为激励我开拓新的研究疆域的重要动力。在伯克利的一年时间里,我选修的课程及阅读的文献几乎全部集中于政治心理学领域。
为什么会对政治心理学产生兴趣?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这个问题常会被人问起,但我自己竟然从未想过。今天想来,兴趣的种子可能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种下了。1988—1989年间,当我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时,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展了一项有关中国地方政府的合作研究项目“四县调查”(“Four-County” Surveys,1990),我作为项目成员参与了其中两个县的调查。调查开始前,项目参与者接受了密集的专业培训。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多位教授亲临课堂,为我们讲授社会调查方法以及这项调查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其中诸多有关民众情感、态度等方面的问题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在走进我们课堂的教授中,就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M. 肯特·詹宁斯(M. Kent Jennings)。詹宁斯教授因在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研究(尤其是政治社会化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1982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后曾任国际政治心理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ISPP)主席(1989—1990)和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主席(1997—1998)。前几年,在与我的电子邮件通信中,他还回忆起他在北大的这段经历。这或许就是我作为一个门外汉不知深浅地闯入政治心理学领地的渊源。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住着不同专业同学的宿舍楼成为我受益无穷的跨学科交流空间。对门宿舍的心理学系博士生王建平学医出身,入读北大后师从临床心理学家陈仲庚先生,当时正关注和研究住院病人的心理状况与身体康复之间的关系。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都去医院做访谈,常常带回一些令她兴奋的发现与我分享。这样的交流一直持续到我毕业。如今她已是国内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也是国内认知行为治疗(CBT)领域的重要先行者。我最早写作的有关人格及政治态度的两篇论文在完成后都曾请她把关,她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与她的讨论也让我更加明确,心理学为理解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政治心理学的关切与心理学以及作为其分支的社会心理学有着很大差异。这一点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心理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心理学分享了共同的学科渊源,但并未像社会心理学那样被视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结束在伯克利的工作后,我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如此,政治心理学于我始终是这样一个领域——这个学科的庞杂远超我的想象和预期,使我至今仍没有足够的信心开设一门政治心理学课程。或许正因如此,我在进行研究时总有一种“玩票”的心态,觉得同“专业研究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的工作任务清单上的其他事项总是可以很容易地把政治心理学研究工作排挤到靠后的位置。结果则是,这项工作竟然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幸好我算得上是一个执着的“玩家”,终于使这项工作有了一个结果,也给自己刚刚逝去的二十多年一个交代。
三
虽是“玩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已围绕人格、态度、舆论、情绪、群体心理等主题陆续完成了多篇论文,从2002年起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天津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其间,这项研究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810020)的支持,而我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逐渐整合于由项目名称“政治心理学:一门学科和一种资源”所概括的思考框架中。
一项研究竟然会断断续续迁延二十多年,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说都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而我则在其间经历了有关不同问题的内心冲突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
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政治心理学的“业余”研究者,却从未想过放弃,反而在有限的职业生涯中将二十多年时间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这种状况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有时也让我不安:是不是偏离了自己的专业领域比较政治学,走得太远了?但看到诸多学术先贤如哈罗德·拉斯韦尔、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鲁西安·派伊、塞缪尔·亨廷顿、西摩·M. 利普塞特、斯坦利·霍夫曼、西德尼·维巴等的研究都曾涉及政治心理学,或其研究就起步于政治心理学,则稍感安心和宽慰了。政治学理论“常常含蓄地建立在有关人们如何思考和感受的基础上”,因而本质上都与心理学相关。那么,有这么多学术先贤涉足政治心理学领域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心理学对于人们理解和应对现实问题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人类似乎拥有一种天赋,即使很少或没有接受过教育,也能发展出运用心理思维本能预测或解释他人行为与心理状态的能力。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相信,这种能力源于正常的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某种原始的或“民间的”(folk)心理学思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通过运用自己的思想资源来模拟他人行为的心理原因,从而预测和解释他人的行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涉及通常被称为“民间心理学/大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常识心理学(commonsense psychology),并提示了心理学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乃至实践功能。
政治心理学一般以某一地域范围内的特定人群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其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因此常常受到怀疑。近年来,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基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比较研究。其中,一些流行的研究议题(如政治信任),以及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如不同国家对待外来移民包括难民的态度)等,越来越多地被置于比较框架中加以探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这一重要趋向,竟使我产生了一丝喜悦,尽管其中的比较逻辑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比较逻辑存在很大差异。
四
“什么是政治心理学”是一个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而“政治心理学研究该如何做”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在二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有时会为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我是在做政治心理学研究,还是哲学研究?这种感觉在进入宽容、政治信任等主题时尤其强烈。直到读了哈耶克的《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1952),看到他作为经济学家在探索理论心理学时,也遭遇了可能在心理学家看来其研究内容“更像是哲学问题而不是心理学问题”的困扰,我竟然产生了某种“救赎感”。
实际上,政治心理学领域一些有影响的研究者,如常被与权威人格研究联系在一起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除了在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有独特贡献外,还是影响巨大的哲学家;至今仍活跃于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且具有重要影响的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本来就是政治哲学家。从学科间关系看,心理学与其他诸多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而政治心理学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从哲学中受益很多。当然,哲学也在诸多方面受惠于心理学,如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的方法就被政治哲学家用于发展一些特定概念的规范表述。在较为具体的层面,这一问题还可以从道德判断、价值判断等对人类心理的影响来理解。事实上,关注精神现象本质、心身关系以及心理与其他物质世界关系问题的心灵哲学(也称精神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已成为当代哲学中极为活跃的一个分支领域。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中,我对政治心理学学科本身的理解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二十多年前,政治心理学还是国内学术界关注较少的一个学科领域,我最初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人们对这一领域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伴随研究的深入,政治心理学作为一种资源的维度日益清晰和突出。基于这样的视角重新审视政治心理学可以发现,源于19世纪动荡的欧洲社会的学科历史本身实际上已提示了学科的现实功能或社会使命。
五
学术前辈与同事的鼓励伴随我走过二十多年的政治心理学探索旅程,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学界及社会所引发的一些关注和讨论,于我更是抚慰心灵的珍贵的学术共鸣。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书以及之前两本著作出版的全力支持,我可以专心研究和写作,无须为出版的事分心费神。特别向先后合作过并给予我很多帮助和鼓励的金娟萍编审、刘金海编审、耿协峰编审、徐少燕编审和陈相宜老师致敬!他们专业严谨的工作使我的作品大为增色,更令我确信喧嚣年代笃定坚守的可贵。家人的爱与支持如影随形,让我的世界四季如春。这些都是我的人生幸运,也使我可以毫不冲突地成为一个乐观的现实主义者和一个理性的理想主义者。
在充斥悖论及不确定性的变革时代,期待政治心理学有关人心与人性的探索可导向个体与社会层面平和安适的心理秩序,以及有助于实现良治的政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