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吴君小说集《阿姐还在真理街》最新出版
追求有社会价值的写作 而非自我陶醉和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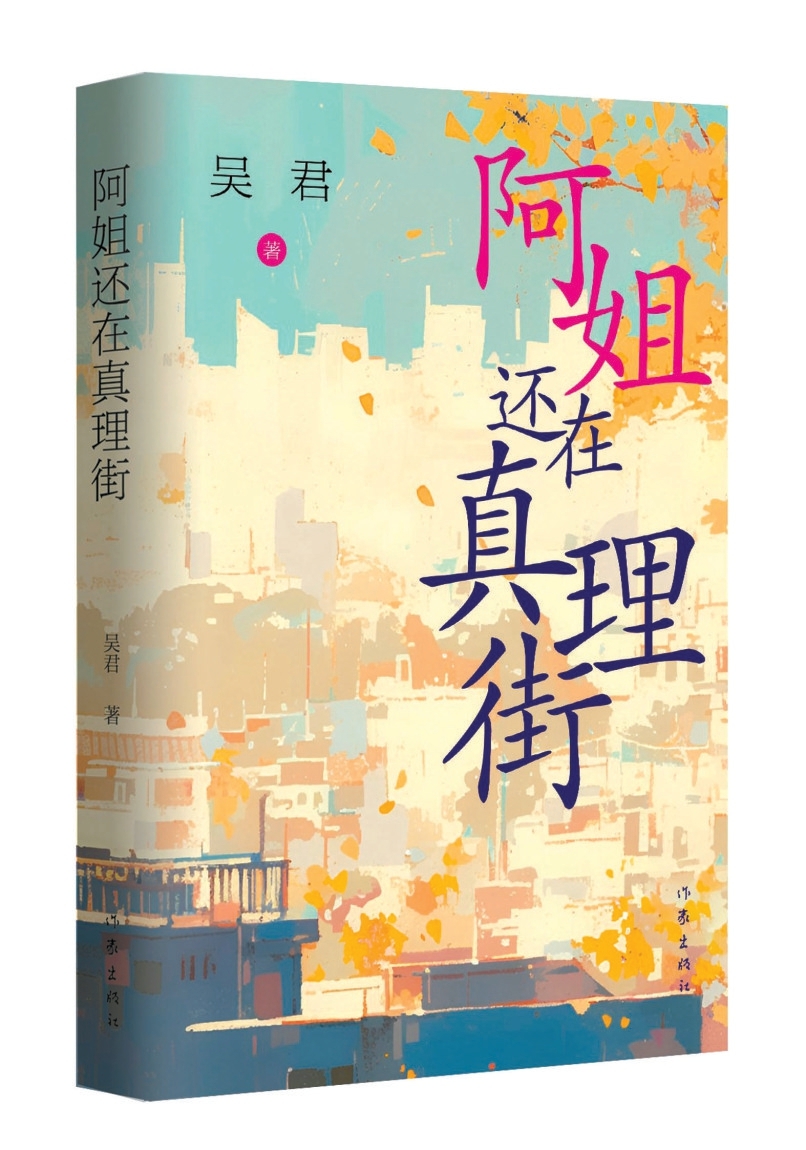

作家吴君曾凭借中篇小说《万事如意》摘得2023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桂冠。评委会赞誉其作品:“父与子、夫与妻的矛盾,揭开了家庭原有的温情面纱,也使每个人自现原形,而这又让他们逐渐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转而切实面对时世流变,以求万事如意。争执激化了潜在的冲突,也提供了和解的契机。由此,一桩看似嘈嘈切切的家常故事,又有平地一声雷的震撼,凸显出作者别致的叙事能力与强劲的艺术腕力。”
作为深圳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笔下鲜活的深圳叙事,为这座城市构建了一份珍贵的“精神档案”,对人性复杂的深刻呈现,是吴君文学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近日,她的小说集《阿姐还在真理街》出版,收录的作品除了《万事如意》,还有《小户人家》《你好大圣》《结婚记》《好百年》《阿姐还在真理街》。这些作品均以深圳为背景,聚焦不同地域、阶层人物在都市快速发展洪流中的生存图景,展现了他们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对生活、家庭、爱情的复杂思考。这些作品不仅关注个体命运,更以宏阔的视野描摹深圳的社会变迁:从工业区的兴衰沉浮到城市格局的转变,从传统文化的坚守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呈现了这座城市在急速发展中所经历的阵痛与转型。小说集中的六部作品如同六幅社会切片,记录了一座城市从破土而出到姹紫嫣红的壮阔历程。
吴君的作品曾屡获殊荣,除了人民文学奖,还有中国小说双年奖、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等。作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深圳作协主席,吴君表示,深圳是一座文学富矿,始终滋养着她;这座城市更像一处无尽的创意源泉,为她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我希望把它持续融入我的书写,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深圳人的心灵秘史。”
用小说勾画自己的深圳精神地图
北青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小说集《阿姐还在真理街》里的这几篇作品,创作之前是否有过一些规划?
吴君:《阿姐还在真理街》里的六篇作品,是我近五年来发表在期刊上的中篇小说。每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或故事背景,都与我关注到的一些现实事件隔空相关。比如《好百年》2019年发表于杂志《芒种》,小说写了二孩政策之后,独生子女群体的处境。《万事如意》描写了在新的商业环境下,厨师、曾经的戏曲演员、酒楼老板三位昔日老友的生活困境和自强不息的市井故事。完成小说的那一年秋天,我已经离开红岭中路,但新安酒楼的招牌让我难忘。这篇小说表达了我对这个群体的美好祈愿。还有《阿姐还在真理街》中,在面对后代们“啃老”时,姜兰惠曾经是社教队员的身份被唤醒了。姜兰惠这样的人像是一颗颗被不经意遗落的种子,历经风雨,重新萌发,再次站立。
在阅读这本小说集时,如果读者意识到,这是一份属于一个作家的深圳精神地图,我的努力也就没有白费。
北青报:感觉“真理街”既是真实的物理空间,也是某种精神困境的隐喻。在《阿姐还在真理街》中,主人公姜兰惠的命运与真理街的兴衰同频。她从教育者到被生活裹挟的妥协者,其坚韧与挣扎不仅是个体的困境,更是一代移民在城市化浪潮中的缩影。创作《阿姐还在真理街》的过程中,您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吴君:与纪实文学完全不同,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虽然我小说中的地名是真实的,与深圳的历史进程也吻合,可故事和人物完全是虚构的。《阿姐还在真理街》源于多年前我了解过的一件事情。当时社教工作队里有个年轻的女孩子,被组织安排到一个村里做反赌反黄反家暴宣传。工作中,她认识了街上的两兄弟,二人同时被女队员的知性气质所吸引,并展开了追求,女队员的命运就此发生了巨变。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震撼。时代洪流中,女性命运转折的故事,我会一直比较关注。
创作过程是酝酿到发酵 而非真假之间的转换
北青报:您在筹备《阿姐还在真理街》期间,用三年时间采访城中村租户,在这个过程中,哪个场景或细节最让您觉得“必须写进小说”?小说绝非简单的“采访实录”,在真实事件与文学虚构之间,您的“转换密码”是什么?
吴君:有一年我和单位同事在街上宣传政策,期间有一位戴着口罩的女性走到我的摊位面前,问我“你们管不管这些”,随后她掀开衣服让我看她的伤口。可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便迅速消失了,我不知道她是胆怯还是感到了危险。望着藏着她的人流,我的脑海里一直是她身上的伤口。
还有一位女作家,她经常在公号里骂前任,诉苦,可是我知道她是在办理离婚期间怀的孕。她们反复横跳的人生没有正确或错误答案,而是迷失和一言难尽。我认为小说不负责给出答案,悬浮的、不确定的人心和不可测的人性,可能才是文学要探究的东西。创作过程是酝酿到发酵而不是真假之间的转换。
北青报:是否也因此,您的作品中好几个故事都结束在“好像什么都没解决”的节点,并没有给出更明确的结局?
吴君:即使是长篇小说,也解决不了现实中的出路问题。在我看来,透出光亮,带来温暖和希望,或许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北青报:在将采访素材转化为文学形象时,您最注重保留人物的哪类特质?
吴君:文学和新闻不同,我不会把具体的人和事放进作品中。遇见的人和事只会引发我的思考和创作思路,不会直接在文字中输出。我认为小说里的人物应该“像”生活里的人,而不能“是”生活中真实的人,否则我将麻烦不断。
小说是写日常 不需要表演
北青报:您的小说使用了一些方言,那么您如何把握方言的使用尺度?如何既保留地域真实性,又不让非本地读者产生隔阂?这种语言选择是否与深圳“移民城市”的文化混杂性有关?
吴君:当然要考虑到接受程度,我保留的多为口语,是日常生活中用到的语言。目的是贴近人物,让人物形象立体丰满,从而达到一种真实的效果。有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认为仅有语言是不够的。无论长篇、中篇还是短篇,都需要结构,都需要思想,都需要与周围环境有关联。
写《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时,责编要我删掉所有的成语,她说你写这个群体,表现的是他们的日常,不能用书面语更不要用舞台腔。小说是写日常,不需要表演,不是炫耀你能背下来多少古诗,掌握多少知识点。高端的瓷器,往往使用的是最朴素的色彩。
北青报:您的叙事风格冷静、克制,但小说中蕴含的情感冲击力却非常强大,您是如何做到在看似客观的描述中积蓄并传递深沉的情感的?
吴君:尽管理性、克制,可内心里我喜欢有温度的小说,不是微波炉里的加热,而是人的体温、内心的暖流。与此同时,我追求有社会价值的写作,而不是个人的自我陶醉和满足,否则与写日记无异。在我看来,记录城市并不只需要新闻和精准的数据,文学也非常必要。当然不能是哲学化概念化的文学,而是描述人在非公共空间里的表现。
北青报:您的作品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如何在写作中平衡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揭示与对文学艺术性的追求?
吴君:关注现实和艺术性不是二选一,更不是对立的关系。我理想的文学作品是强烈介入现实的那一种,比如《暴风骤雨》《子夜》。文学只有和现实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这类话很多作家都说过。卡夫卡关注的是昆虫吗?当然不是,是家庭关系吗?也不是,他反映的是人的根本处境,被极致异化的人生。
成长就是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和事
北青报:您认为文学在记录城市史时,扮演怎样的角色?
吴君:文学应该和城市同在、共生,作家虽然隐身在人物之外,读者却可以透过作品找到线索,发现作家的立场,听到作家的声音。
北青报:女性写作常被标签化,您希望读者抛开性别预设后,还能在您的作品里看到什么?
吴君:希望读者能看到具体语境下,人的精神状态、真实的境遇、大时代下个体的命运。
北青报:您如何看待自己创作脉络的演变?业内评价您的创作“稳定强劲,质量上乘”,您是如何做到的?
吴君:我的创作一直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在创作上,任何作家都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打破执念,调整认知。我认为写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在写的过程中解决的,而不是想就可以了。就像你学了很多游泳的理论,可是没有下过水,呛过水,怎么能学会呢?这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尽管我会认真对待每一篇,但同时我也不纠结在具体的某一篇,因为我是宏观地写作,完成我一个整体写作计划,具体的每一篇只是我写作版图上的一篇,它代表的只是我的一个时期。写作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前提是认准了这条路,然后坚定不移。
北青报:您说“写作是一个作家暴露短板的过程,也是一个作家认识自我的过程,是梳理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不断成长的历程。”请您举例具体讲一下。
吴君:作家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状态,包括稳定的内心,尤其是小说作者。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储备不足都将影响作家的心态和作品的深度。记者和作家不同,记者的工作是对外,而作家是面向自己。小说可以虚构,而作家的诚意无法虚构,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是漫长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实践,要在生活中扎根下来,在一次次磨炼中掌握创作要领,并贯穿到整个创作生涯中。
我曾经在电台做过6年采编工作,记者这个职业习惯帮了我。在书写他者的时候,自然会被人物带着成长。比如《同乐街》里的陈有光,如果生活中我遇见他,有可能不予理会,可是要写他,就必须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为他的行为找到合理性。过程中,会理解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和事。我认为这就是成长和进步。
北青报:您做过记者,当过公务员,这些经历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影响和帮助?您喜欢的作家是哪一类型?
吴君:我认为任何职业都会对人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适当的焦虑和紧张感可能有益于写作,工作越忙越想写点什么来缓解——写作是我的另一个世界。说到焦虑问题,我认为谁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我的职业让我没有那么多的任性,也没有那么多姿态,而是多了一些机会了解文学之外的人和事。古代文人中我比较喜欢曾巩。
写作让我踏实 让我开阔
北青报:您平时是怎么为写作做积累的?
吴君:在我看来,活着就是深入生活。写作不能只靠想象力,你需要素材,就像厨师要有新鲜食材。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每天的所见所闻不可能让他无动于衷。体验生活很难代替设身处地、置身其中。创作时,作家应该向演员学习,把角色的苦当作自己的苦,把人物的经历视为自己的经历。事不关己的话,极有可能出现隔岸观火的结果。我只有在写作时才是作家,其他时间,我只是一个职业妇女,和其他人一样,经历所有的一切。我希望我所了解的生活,不是二手的生活和过滤的生活。
北青报:对于现在的年轻读者,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帮助吗?
吴君:我认为年轻读者未必需要前辈作家的意见,他们这代人有自己的方式进入世界。我的小说只提供一个角度,让他们看到另一位作家的盲人摸象、一孔之见。
北青报:写作对您的意义是什么?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吴君:写作可以让内心变得踏实,会更加包容和开阔。未来的计划就是继续完成我的深圳叙事。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