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兼具科学观察与诗意表达
——读阿来长篇非虚构作品《大河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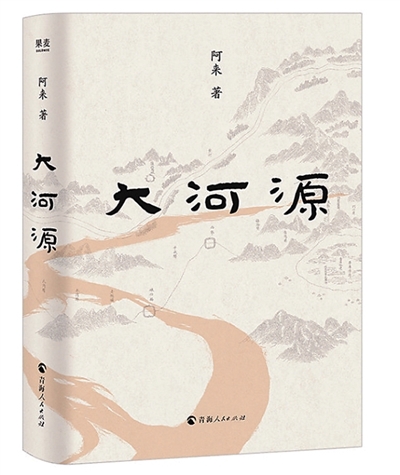
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大河源》,是作家阿来深入黄河腹地,在科学与文学、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互渗中,以冷峻而又富于温情的笔触书写黄河源的一部作品。该书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演进轨迹,挖掘黄河的文化象征意义,探寻人与自然复杂关系,是博物书写、历史书写,也是生态书写。
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索河流的源头”;同样,人文学者也鲜以科学的观察与思维对河流进行知识性书写。而阿来兼具博物学家的气质与诗人的气度,不仅拥有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与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又善于用诗意的笔触捕捉自然之美,赋予世间万物以鲜活的生命力。因此,阿来笔下的黄河书写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融合科学与人文,广泛吸纳并综合运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多学科知识与方法。
首先,阿来运用科学方法,对黄河源区的自然物象展开博物书写。甘青铁线莲、祁连圆柏等花草树木的生长习性及形态特征,巴颜喀拉山、若尔盖大草原等典型地貌的形成机制与变迁特征,黄河源区复杂的水系结构特点及其动态演变等,都被作家以知识性写作的方式进行了精准描摹。与此同时,阿来的文字中蕴藏着灵动的诗意,他写初寻黄河源时遇到的景象是“风从天上撕扯下来那么多云雾,一下就把山头和一行人包裹起来”“低头,看见脚边青草间蹦跳着颗颗雪”。阿来赋予自然之物人的性灵与情感,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意。通过对风的“撕扯”及其对人的“包裹”等拟人化笔法,展现了风的肆虐与压迫,勾勒出风雨骤至、天地混沌之象。而“蹦跳”一词,则使雪变成在青草间欢快地跳跃嬉戏的小精灵,打破了风雪带来的压抑感。在众多关于黄河的书写中,《大河源》宛如“黄河大合唱”中一个独树一帜的声部,以其特有的旋律与节奏,奏响了科学与文学的和鸣。
《大河源》也是一部传统与现代共生的深情传记。作者以“吾土吾民”的情怀,溯源黄河源头,唤醒历史记忆,挖掘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象征意义。他在书中广泛援引黄河源头地区丰富的县志史料、严谨的考古资料、珍贵的史前石刻以及浪漫的诗歌神话等,找寻古老黄河的青春容颜与鲜活记忆。通过对宗日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黄河源区古文化遗存的书写以及对茶马互市、汉藏和亲、古驿道开辟等史实的论述,阿来论证了自古以来多民族交流与融合的事实。此外,阿来还以现代眼光审视当下,对生态保护提出建议。《大河源》既钩沉历史记忆,又洞察时代症结,不仅是黄河历史文脉的记录,更是一部具有现代意味的生态启示录。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可以说是近年来阿来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西高地行记》《去有风的旷野》等散文游记,实地踏勘自然,感悟人情物理,在行走中体悟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云中记》等小说,通过艺术想象构建人与自然的互动场景,展现灾难面前人与自然力量的博弈。《大河源》是这一创作脉络的延续,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所说:“对人的反省,是《大河源》最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在这部作品中,阿来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叙事模式,秉持众生平等的理念,以饱含温情与诗意的笔触,对黄河源区的湖泊、草甸、高山、花鸟、树木等自然万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呈现。在作家的认知里,“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也是所有生命共生共荣的世界”。他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将人类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中,引我们重新思考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在此意义上,《大河源》是一部具有生态思想启蒙意义的作品,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一部力作。
(作者:张傲、张凡,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