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刘伟
中秋来临,惯例有相思寄托。偶尔看见友人发来王献之书法“中秋帖”,看到那句“中秋不復不得相……”,想到胡彬彬教授辞世已两月有余,不由悲从中来。
回想9月10日,暑热已退,我再一次去“乡庐”。那天,汽车穿行在蜿蜒的乡间小道,道路很窄,路侧时而有村民的单栋民居,时而有枝蔓交错的树丛、池溏和错落的田地。夕阳余晖,景色虽好,我心情却很沉痛。

胡彬彬
我第一次去“乡庐”,是2022年夏季应彬彬先生所邀。“乡庐”是彬彬先生在家乡湖南双峰县乡下修建的一个院子,也是一个乡间美术馆。我去的时候正在建设中,白色主体建筑凹字型,建于小山坡上。登临屋顶,丘陵起伏,炊烟袅袅,视野开阔。他给我说,退休以后就回这里居住,“乡庐”收藏有一些传统村落的实物,将其展示出来,欢迎有志者来考证、研究并相互探讨,延续自己的学术梦想。同时,也将向附近乡村、远至县镇的居民和中小学生开放。自己当讲解员,做一个反哺家乡的“乡贤”,把传统文化的种子种到乡人和孩子的心灵里。
然而,7月22日,接到噩耗,胡彬彬教授走了!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相信是真的。两个月前,我有一本新作出版,微信给彬彬先生,言欲奉上一本请教,他回复说寄到中心即可。6月10日我微信问候他“无病无灾,大吉大利”,他还有回应。之后,便再无信息。冥冥之中,在7月22 日,我给彬彬先生的弟子吴灿教授发信息:“最近我给彬彬教授发信息都没有回复,他身体情况如何?烦请告之。”孰料,吴灿悲痛地回复我:“胡老昨晚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一个月后再发讣告。”而且特别叮嘱我不要过来,说彬彬教授病重期间不让告诉外面的任何人。去世后马上火化,骨灰撒到黄河长江。
彬彬先生走得那么突然,洒脱一去,仙凡两隔。以至于到现在,我浑然不觉他已逝去,提到或者看到他的名字,我耳边仍会响起他沙哑而宏亮的湘音。这个走遍中华大地的田野考察者,这个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者,这个全身散发着咄咄逼人气息的学者,就这么走了?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呢?
哀哉!孤帆远景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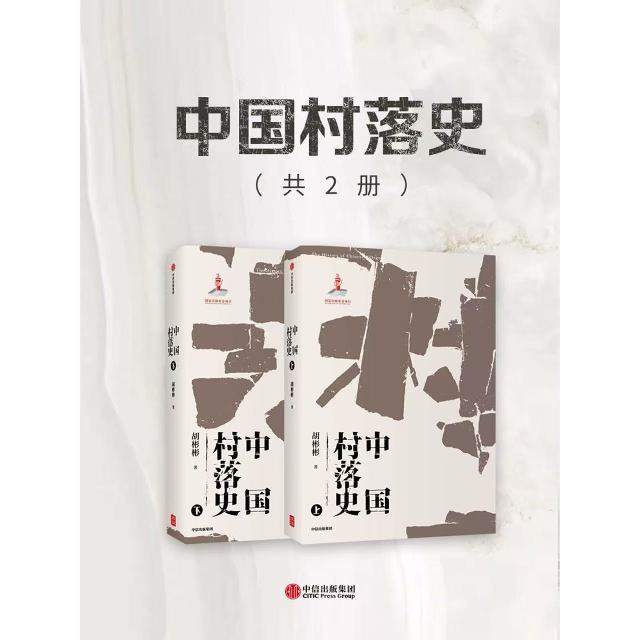
《中国村落史》
我与彬彬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24年11月23日,那是在“第二届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高峰论坛”会上。会上同时举行了《乡愁里的古村落》新书发布会。煌煌十卷,图文并茂,由彬彬先生的团队完成。当时见到彬彬先生,他身形比往昔消瘦了许多,虽言语清晰,然步履已呈老态矣!我黯然神伤,只是嘱他多保重,择时再去“乡庐”拜访,一起品尝乡间土菜,一起海阔天空。未想,那日作别,竟为最后一面。痛哉!会后数日,彬彬先生还给我来信息,咨询《密宗五百佛像考》一书。我回复说自己有《三百佛像集》(北京木刻版重印)和《五百佛像集》(瑞士苏黎世大学博物馆藏),彬彬先生所说之书,我查了一下,是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原名《密宗五百佛像考》,后再版改名为《藏传佛教圣像解说》,随后我寄了一本给彬彬先生。
与彬彬先生相识,缘于2012年5月光明日报记者龙军的一篇报道《胡彬彬,古村落研究的拓荒者》。当时,胡彬彬是岳麓书院教授兼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龙军在文章中介绍,“胡彬彬的足迹遍及祖国山山水水,搜集古村落文化遗存等实物以及图像资料,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田野考察札记,拍下了三千多个胶卷和近二十万张数码照片,手绘了近千张古村落建筑样图,撰写研究专著10部,在海内外核心学术刊物发表各类研究论文50多万字。”世上专家千千万,但真正的学者,除了学习书本上先贤的教诲和经验,还要致力于考据和实证,而后者更为可贵。“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我立即对胡彬彬有了兴趣,很快邀请他在岳麓书院做了一场学术报告,题目是“小村落,大文化”,全文整版刊载于光明日报,此文在当年学界的反响,毋庸赘述。
彬彬先生在2008年创建的“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获批为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组织国内专家考察该中心之后,评价道,“所藏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实物、文献与图像资料,不但翔实可靠,且富有权威性,弥足珍贵。以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创新方法与手段,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整体研究,是填补我国人文科学领域缺陷和空白之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我曾数次到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藏馆参观,藏品之丰富,类别之齐全,专家所评不虚也!
面对迅猛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保护、深入研究类型丰富的乡村文化遗存,彬彬先生提出,“村落是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家庭是民族最基础的构成单元。由于村落文化具有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并承载了中国久远悠长的文明史,因而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他认为,“要从宏观上来研究村落社会,解决农村、农业、农民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由此引申到事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保护与研究的重大问题。”随着彬彬先生的逝去,他对中国村落文化研究和保护的洞见、对文化传承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对传统村落文化研究和保护的理论贡献,其价值之巨大,如今愈发显现。可以说,在浮夸、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盛行的当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胡彬彬的逝世,不仅是湖南,而且也是中国学界的重大损失。
就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而言,彬彬先生不仅有坚不可摧的文化自信,而且有付诸艰苦卓绝的实践。与之交往,可真切地感受到彬彬先生儿童般的天真,自信,还有固执。人不可貌相,或许是常年田野考察,他皮肤黢黑,皱纹满面,眼里闪烁着乡人的狡黠,话语透露出学者的博学,无怪乎乡民尊称其“村长教授”。他抽烟不喝酒,对赏识其才华的领导和同仁,彬彬有礼;自己不修边幅,对学生亦不甚绳束,但发起脾气来,又如怒目金刚。彬彬先生家学深厚,自幼好学,涉猎广泛,修得满腹经纶,由县府小吏获评为文博类教授,直抵学术大雅之堂,放眼全国,鲜矣!他性格耿直,对乡村消亡、文化损毁现象,常出犯上犯忌之语,不平之气,鸣于文字。虽时有官员和专家白眼,亦是我行我素,矫矫不群。他的身上,散发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既有费孝通的书生本色,也有梁漱溟的士大夫执拗。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对传统村落文化,坚持田野考察与文献考据并重,在理论上具有开创性建树。
中国的文化是活的文化,还在继续生长。尤其是那些生产方式、居住环境、生活习俗保留比较完整的传统乡村,只要深入其间,便能处处感受到乡村居民的性格特征、地方文化积淀(道德观、审美观和世界观)、家族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宝贵的部分。彬彬先生与我许多见解心有灵通,惺惺相惜。参加学术讲座或论坛,他都要呼吁:“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和全面深入研究,既是当前我国文化传承、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需求,更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城市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必须直面的课题。”彬彬先生与我多次谈到,把握中国国情,须从中国乡村入手,从田野考察的困难艰辛中,披沙沥金,获得学问和经验。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但农村、农业、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研究这个主体,村落文化不可或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但具有丰富的内涵与特质,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良好的传承性。作为传统活态文化传承的载体,村落功不可没。”也许是专事村落文化研究,彬彬先生对民族民间文化情有独钟,他多次去西北西南采风,其中两次还让我专门介绍西藏地方风物风俗,当地文化遗存现状。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十八场主讲嘉宾胡彬彬
结识彬彬先生之后,但凡到长沙,我必去拜访。前些年,彬彬先生约请我到中南大学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客串教授,带几个博士。我自揣庸愚,学识浅薄,且精力不逮,不敢当此重誉,既拂先生美意,也误可畏之学生。他笑着说,新闻记者与文化学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你们专注新近发生的事,我们专注过去发生的事,调查研究的手段是相似的,对中华文化的敬仰也是一致的。我,一个记者,钟情于祖国河山,兴趣于史志地理、凡人故事,热衷于城市乡村采访,然鲜有作为,愧乏贡献;他,一个学者,独宗村落文化,专注模山范水,由湖湘而天南地北,凡宗祠牌楼、碑刻壁画、民间技艺、传说逸闻,徜徉于田野,揖问于乡民,积学储宝,研阅穷照,筚路蓝缕,厚积而薄发,既拓宽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的领域,也极大地提升了村落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
2017年12月,胡彬彬主编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蓝皮书》在北京正式发布,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与保护的蓝皮书。
2018年4月,胡彬彬与吴灿合著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概论》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对村落文化进行理论概述的教科书。
2021年8月,胡彬彬的百万字专著《中国村落史》(上下卷)正式出版,作者基于30余年对5000多个传统村落的田野考察,结合考古和历史文献,系统梳理了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现代社会转型期的村落发展脉络。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乡村通史。
彬彬先生时常感慨有一种无形的使命催促着,时不我待,“我的宿命是保护传统古村落。”“若我在田野村落中逝去,请不要悲伤,这将是我最好的归宿。”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再到“乡庐”,斯人已去,房舍俨然,物是人非,令人唏嘘。那天,我在彬彬先生灵魂寄附之地,献上一束鲜花。人生逆旅,世事无常,未能在彬彬先生病中时去看望,未能在他最后的时光对坐品茶(哪怕静坐片刻也好),唯留遗憾,于习习晚风中。
今年中秋夜,云层厚,月隐现,想起唐诗《中秋月》:“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谨以此寄托哀思!
2025年中秋夜于北京寓所
(作者为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