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中国文化在近代并没有表现为一味地衰落,更没有解体,而是在迎接光明,走向复兴——
从黄昏到黎明: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嬗变历程
张昭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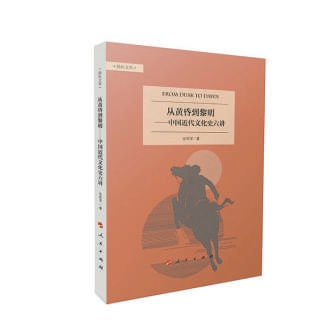
《从黄昏到黎明——中国近代文化史六讲》,张昭军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拉长时间段看,近代文化只是其中的一节。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角度,将中国文化史分为三期:第一期,自邃古以迄两汉,国内诸族交流融汇,创造出独立的文化。第二期,自东汉以迄明季,佛教东来,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由抵牾而融合,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道家、佛家文化为补充的传统文化。第三期,自明季以迄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渐次输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由冲突而交流、融合,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文化。
近代文化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又赋予中国文化以崭新的时代精神,展示了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活力。作为中国文化长河的一节,近代文化吸纳了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成分,但后者并没能取代前者,中国文化的主体没有变,中国文化在近代奔腾向前的动力主要是来自自身。况且,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无论就体量还是势能而言,其命运和前途绝非外来文化所能够左右,更不可能舍己从人。
孟子曾以“一治一乱”来描述上古历史的演变,“大道之行”则治,“大道既隐”则衰。汤因比则将历史比作时间织机上来回穿行的梭子,看似循环往复,却能够编织出不同样式的图案。这两种说法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人类历史螺旋式演进的状态。受此启发,《从黄昏到黎明——中国近代文化史六讲》一书尝试以“从黄昏到黎明”为喻,解释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嬗变历程。
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恰如从黄昏到黎明,经历了一个漫漫的长夜。黄昏是时间的界标,它既可以视为一天的结束(当然不是时间的终结),也可以理解为新的一天的开始:黑夜是白昼的准备。东方既白,回望历史,中国文化在近代并没有表现为一味地衰落,更没有解体,而是在迎接光明,走向复兴。
“贞下起元,往而必复。”近代文化不仅构成了延绵不绝的中国文化的一环,承前启后,推陈出新,而且放眼世界文明发展史,也容易让人生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慨。在西方人的词典里,oriental(东方)、occidental(西方)这对概念分别源自拉丁语oriens(太阳升起)和occidens(夕阳),对应“清晨之地”与“傍晚之地”。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将“东方”视作人类文明的“起点”和“过去”,“西方”视作人类的“现在”和“归宿”;用“东方”代表遥远的天堂,西方代表“现世”。黑格尔由此出发,甚至自豪地宣称,世界精神的“太阳”虽由东方升起,但东方国家只是人类历史的幼年期,世界精神的“太阳”最终是降落在了体现人类成熟和力量的日耳曼人身上,从而实现了其终极目的。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表明,世界精神的“太阳”并没有永远地驻留在西方,西方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中华文明正再次实现伟大的复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日出东方催人醒。”长期以来,提及中国近代史,映入人们脑海的往往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衰落、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这段历史记忆刻骨铭心,不堪回首。但全面地看,近代史不仅仅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还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蕴涵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历史表明,民族复兴才是近代历史的方向。借用恩格斯的话说,从“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阶段,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